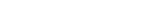巫蛊之事,由始至终不过一日,其实漏洞是有的,但上头的人没打算查,下面的人也没胆子说话,待眼看着慧妃哭闹不休的被拖走,各自心思的一众妃嫔离开后,我才扭过头去看景熠。
这个近十日来不曾来坤仪宫的帝王俨然是有话要说,我在心里犹豫了一下,不知道是该装模作样的检讨失察,还是直接问他有什么吩咐。
好在景熠没有耽搁,开口时直接跳过了慧妃的事:“阑珊要见你,沈霖那也有事,你去一趟。”
我愣住,没想到这话会从他嘴里说出来,明明前些日他还咬牙切齿地威胁说不想看到落影出现,为何今日就能出尔反尔的叫我出宫。
“叫鸿雁跟你一起,”见我发怔,景熠继续道,“天黑前回来,不要再惹出什么麻烦。”
“不用——”我早对内宫路线十分熟悉,便是没有傅鸿雁,也绝不会有问题,我刚要拒绝,一眼看到景熠警告意味严重的眼神,当即把话吞了回去,点头,“好。”
他淡看我一眼,道:“短期内朕不希望容成家再出什么事端。”
身为皇后,要进出宫当然不会像原先那么随意,第一个要掩饰的就是坤仪宫这边,好在景熠的单独留下给了我极好的借口,叫水陌关了宫门,对外只说皇后受到了皇上的斥责,不见任何人。
现在宫里头几乎人人都认得我,想溜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,不过有景熠的安排就方便得多,,直接一顶小轿抬着,随便编了个内命妇家眷,就由傅鸿雁领着大摇大摆地出了宫,。
出了宫,路上总算寻到机会问傅鸿雁到底是有什么事,能让景熠亲自安排我出宫。
“逆水堂选定了新堂主,沈霖说无论如何你也得露一面,”傅鸿雁对我依旧没多少好气,看我一眼道,“你多了不起,躲了半年,露一次面就把陆兆元免了,新堂主上任,你不出现像什么样子。”
与平日里动辄王爷皇上不同,傅鸿雁直呼沈霖名字的时候,就代表他是在以倾城一员的身份说话,其实傅鸿雁也出身逆水,不过是除了我以外,堂内没有人清楚他的身份和职责,见过他的都不多。前面这几年,对倾城来说是我和沈霖的一明一暗搭档,而相对景熠,我的搭档就是傅鸿雁。
“哦,”我认命地点了头,心里想着还是不对,便是为了这个事,景熠又怎么会扯到容成家身上去,于是追问,“还有呢?”
“还有——”傅鸿雁此时神色严肃下来,略皱眉道,“阑珊知道你的身份以后很生气,说要去杀了容成弘,城主不让,两人打了起来,沈霖没拦住。”
“啊?”我听了一惊,“什么叫没拦住?很严重么?”
“城主在王府呢,沈霖说守在身边安全些,”傅鸿雁叹口气,“你见了就知道严不严重了。”
我默然,凝神不解:“怎么会这样——”
“怎么不会?”仿佛嫌我大惊小怪一般,他哼了一声,“他们俩动手,谁敢拦?谁拦得住!”
王府很快就到了,唐桀果然伤得很重,费力撑着要说话,被沈霖拦了,我在屋里陪着坐了一会儿,起身出来就看见了阑珊。
阑珊话也不说,仗剑就劈过来。
对她我可不敢大意,自己长达半年的杳无音信还未让她释怀,乍降的惊人身份又再一次激怒了她,真动起手绝不会讲究什么分寸,里头重伤的唐桀就是活生生的例子,更何况此时我手边还没有暗夜。
也不敢解释,忙着旋身就躲,阑珊紧黏在我身后,不给我撤出去的机会,顿时就是险象环生,逼得我只好大着胆子以手指弹开她近在咫尺的剑锋,“铛“的一声震得我整个儿右手疼到发颤,忙着低叫求饶:“阑珊——”
阑珊这才停住,却不肯收剑,盯着我皱眉:“你的剑呢?”
我脱离危险,冲着她笑一笑:“没带着。”
“谁允许你可以不带剑了!”阑珊面上看不出喜怒,沉声,“是没带,还是他不让你带?”
“也没什么分别,”我依旧淡笑,“是我自己选的路,就要坚持走下去。”
她盯了我一会儿,把剑收起来回身往外走,我知道她有话要说,默然跟在后面。
“从你娘严密守着不说,我就一直猜测你爹是个大人物,”许久,阑珊才淡淡开口,“只没想过,竟然会是容成家的。”
“是啊,”不等我说什么,她又顿悟了一般,“还有谁家能让她连我都不敢说呢。”
“锦言,容成锦言——”说着她转过身瞪我,“你了不得啊!以为皇后是人人都能做的么!”
“当然不是,”我沉默片刻,抬头对上她的眼睛,“阑珊你说过,只要能达到目的,我们可以不计较手段。”
她冷哼一声:“不错,但前提是能达到目的,你就不怕弄巧成拙,他依然不要你,倾城你也待不下去?你就不怕我知道了那个负心汉是谁立刻去杀了他!”
“怕,”我笑得有些凄凉,“所以我等了那么多年才敢冒这一次险,我爱他爱了好多年,又怎么能接受一朝成空的结局。”
停一下,我道:“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庆幸自己姓容成,我好不容易用一个他无法推开的身份站到他身边了,你忍心要我再一次成空么?”
“言言,你真的跟你娘很像,”好一会儿,她终于叹一口气,“希望你不会后悔。”
“我娘都没有悔,我又怎么会,”我顿一下,“她说过,如果喜欢,就不要放弃。”
“她这样说?”
见我点头,阑珊微闭了下眼,有些唏嘘,“我总是比不上她。”
“她用爱支撑着自己,你却把自己禁锢在恨里。”
我第一次当着她的面评价她与唐桀的感情,眼睛飘向唐桀所在的屋子,“为什么这么做?”
阑珊看我一眼,答非所问:“你这么一闹,景熠气坏了吧?”
我笑笑:“难为了他的定力。”
“所以啊,不这样他能放你出来么?”她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,“至少也能让他了解你瞒这么多年是迫不得已,早几年容成弘要是死了,兴许他跟容成耀早水火不容了,哪还能拖到这会儿让他谋算?”
“正因为如此,早几年你知道了也不会去杀我爹的,”我明白阑珊想帮我一把的苦心,感念之余,依旧担忧,“你总是下这么重的手,就不怕有一天真的把他杀了?”
阑珊哼笑一声,转过头去不说话,少顷道:“他死了,记得叫人通知我一声。”
送走阑珊,我回到屋里,沈霖留了傅鸿雁看着唐桀,瞄了一眼我暗自揉捏的右手,没说什么,带我去见逆水堂的新任堂主。
我点头跟他去,除了唐桀阑珊,其他人并不知道沈霖的真实身份,见面自然不能安排在王府内,我们从后门出了王府,绕到不远的一处私宅的花园里坐下来,沈霖吩咐了人去知会。
从今日见到我一直到两人独处,沈霖都没主动与我说什么,只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,没有不悦也不见热络,我看着眼前的他,知道尽管阑珊的怒火半真半假,但沈霖的隔阂却千真万确。
尽管沈霖的温和亲切只表现在他愿意表现的时刻,他毕竟上是一位尊贵王爷,下是倾城的掌权者,又怎么可能一直平易近人?然而我也是到现在才明白,面对刻意生疏起来的他,会比面对景熠更难找说话。
还没想到要说些什么,只见花园拱门那边过来了一行人,一眼扫过去,宫怀鸣和迎风阁的四个堂主都来了,另一个面生的,想必是逆水的新堂主。
我和沈霖迎过去几步,众人站定,我先冲着宫怀鸣那五个人淡笑:“很久没见你们一齐出现了。”
宫怀鸣点头道:“逆水堂有事,自然要聚齐的。”
他身后的几人随即附和,只有岳泽堂堂主温嵘一脸忿然,只是碍着场面一时没说什么,
岳泽堂在迎风阁负责招众,可谓是人手人脉最广的堂口,之前找我的差事自然是落在他们头上,想必为这个没少受宫怀鸣的苛责。
我略带歉然地看了温嵘一眼,转过头去把目光落在那个肃然沉默的新面孔上。
沈霖在一旁道:“这是逆水新任堂主,萧漓。”
我依着身份点头示意:“萧堂主,我是落影。”
那个严肃中带几分深沉的年轻男子微一挑眉,仿佛有点失望:“你是落影?”
不等我开口,温嵘趁忍不住插了话:“是啊,让我们找了半年!你可不要小瞧了她。”
顾绵绵还是喜欢添乱,她神色夸张地凑过来:“落影,我记得当年陆兆元也是这个表情。”
说完又冲萧漓道:“萧堂主,依着规矩,你是可以跟落影过过手的,输了也不丢脸!”
几句话这么一说,萧漓脸上就有点挂不住。我见状不能再放任她说什么,把笑收了去看宫怀鸣:“宫阁主,你不管管么?”
宫怀鸣没什么表情,给了我一个一本正经的答复:“惩戒是荣峻堂的事。”
一下子把话题上升到惩戒的高度,宫怀鸣可算将了我一军。
“看阁主说的,哪有那么严重,”我很快笑笑,“只是逆水新近换人掌舵,我与我们堂主有些事项要说,还请几位回避一下的好。”
说罢我悠悠地看向顾绵绵,知道赶她走才是踩中她的死穴,果然她立刻皱了脸,一副求饶的眼神飘过来,见我不理,又转过去冲萧漓抱拳,声音温腻:“绵绵只是一时心急,方才失礼,还请萧堂主见谅。”
温嵘见状也随着抱拳,虽不说什么,总是示了弱。
一来一往,萧漓也看出了端倪,此时欣然笑道:“不妨,只是不知顾堂主在心急什么?”
顾绵绵总是不同于常人,闻言毫不遮掩:“逆水堂排行第一方可挑战落影,前头一个我亲眼见到被她杀了,萧堂主还明知故问。”
“既如此,”萧漓哈哈一笑,坦然道,“我这特权不用岂不是浪费了!”
“倾城落影天下闻名,如你所说,输了也不丢人,”萧漓转头看向我,举剑抱拳,“那萧某就大胆讨教一下了。”
我迟疑了一下,没有办法拒绝,只得轻轻点头:“好。”
眼看着细水出鞘,我扭过头去:“绵绵——”
顾绵绵随身并不带剑,把一旁宫怀鸣手里的纹风抽出来抛给我,嘴上不停:“你这个借剑的习惯什么时候能改一改?”
我抬手接下,知道她把纹风给我是居心叵测,宫怀鸣不闪不躲地放任她也其心可居,瞥他们一眼不说什么,转回头对萧漓道:“堂主请。”
萧漓的剑法原本不是倾城系,看得出是做了堂主才新近改用的,使起来并不纯熟,倒让我有点犹豫了,纹风剑沉,只有配合举重若轻的风系剑法才能发挥作用,于是勉强着使了水系,费力之余希望萧漓看得懂。
果然不出十招萧漓就放弃了并不惯用的倾城剑法,改了他原有的恢弘大气的自家套路,很快我就发现这个萧漓的功夫非常好,出手极稳,后劲深远绵长,比原堂主陆兆元还要略胜一筹。
对付这类的对手只能速胜,若是持久战,我就胜算不大了。
然而此时我又不能尽全力速胜了他,没有必要也不合情理,只得拖了一阵子,两百招不到便示意作罢。
萧漓也不恋战,见我后撤一样见好,束剑与我示意。
“堂主好身手,”我率先开口,把剑还给宫怀鸣,意味深长道,“宫阁主又有劲敌了。”
宫怀鸣似笑非笑地接过剑去没说什么,倒是萧漓十分坦荡:“你就别自谦了,拿纹风当细水用,至少就打了三成折扣,还能跟我走过二百招的,你是第一个。”
“若是换了你顺手的剑,想来不至百招就能拿下我,”他说着抱拳:“如此要多谢落影手下留情了。”
“堂主谬赞,”我微微讶异,宫怀鸣都看着不吭声,萧漓能如此看轻胜负,倒让我心里生了敬佩,也不再客套什么,“我以后可能不大方便露面,所以劳烦堂主能好好稳住逆水,不要经常把我叫出来才好。”
话说得很清楚,我不想常常被挑战,所以你萧漓最好稳居逆水第一,不要轻易被人打败超过了去。
萧漓淡笑点头:“萧某自当尽力。”
我转头,后面的话还没出口,突然感到身后一阵疾劲剑风袭来,伴随着沈霖的声音:“这么多人大老远跑来见你,这样简单收场可不行!”
一瞬间那几个看热闹的表情都十分精彩,我也顾不上回头说话,忙凭着感觉闪了一招,手上没剑有点狼狈,俨然沈霖是想逼我亮出暗夜来,只可惜我根本没带着。
好在萧漓就在眼前,我伸手的同时他已经把细水抛了过来,右手接住,提气凝神,拆了几招过后我明白沈霖是真的生气了,他一出手就毫不留情,把功力发挥了十成十,他的剑本来就快,此时更是只剩了一团青影。
我不知道在场众人是不是见过,至少我在这里是第一次面对沈霖这等阵势。
快剑快解,我再也没有思考时间,也顾不上什么剑系,下意识的杂乱地抵挡上去,直到将霜色剑影彻底混入了沈霖的周身,才逼得他把速度降下来。
我也庆幸手里拿的是细水,若是方才的纹风,恐怕此时已经接不上气息了。
旧伤不理的隐患总算出现了,胸口愈发痛得厉害,右手方才被阑珊的剑气震伤,还在刻骨的疼。我一时半刻抽不出身,又不敢继续拖延,咬咬牙,瞅准时机,纵身一掌把他逼退一步,趁着这个空隙将细水换到左手,再不掩饰保留什么,只避了几记杀招不用,剩下的全都倾力迎上,撤掉防御,以攻为守,终于在双剑“叮当”一声交错之后,两人各自退开。
又是一个看起来旗鼓相当的结局,实质却与方才完全不同。
众人愣了一瞬,说话的是宫怀鸣:“能得此一见,当真不虚此行。”
“怎么跟谁都是打平,”顾绵绵明显有点惊讶,跟着道,“落影你原来是左手剑——”
我一时无语,原地低头了一会儿才勉强压住胸口的气血,扯动一下嘴角:“这回总算对得起各位了。”
说着我双手把细水托起来送到萧漓面前:“多谢堂主借剑。”
萧漓接过来,看着我道:“不愧是能进宫行刺还全身而退的,萧某大开眼界。”
我一怔,很快笑一下,转头对顾绵绵开口:“绵绵,查下半年前售卖的所有噬魂的去处,给我一份名单,特别是有可能涉及朝廷或流入皇宫的。”
顾绵绵一愣:“怎么?”
“有人用它来对付我,”我停一下,没有流露出什么倾向,“查到了不要打草惊蛇,告诉黎原就行了。”
她“啊”了一下,脸上当即就有点变色,怔怔点头。
沈霖自始至终都没说什么,那几人离开后,我扭过头去看他,刚要开口打破沉默,就听见他皱眉问我:“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?”
我一呆,自认掩盖得并无破绽,没想到还是会被他看出来,恍然:“啊——”
“还要瞒么?”沈霖盯着我看,“方才你的气息始终都接不上,换手出招是撑不下去了吧?我若不肯停手,你会如何?”
“我能如何,”我愣一下,些许疲惫涌上来,勉强笑笑,“大不了叫你刺一剑出出气。”
沈霖有点急:“你以为我是要跟你过不去么!”
默然片刻,我仰起头迎上他的目光:“沈霖,我知道是我不好,可是我被逼到那个份上,我能怎么办呢?只有一次机会,我唯有放手一搏。”
“放手一搏?”沈霖眼眸收紧,“你是把他当敌人还是把我当敌人?”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——”我低头,不知道该怎么表达,“可是这件事,他坚决阻止,我一意孤行,如果我告诉你,你会怎么做,帮他还是帮我,无论哪一种,你都会为难吧。”
吸一口气,我低声道:“我不想你为难,也实在承担不起功亏一篑的后果,所以只能尽可能瞒下来。”
“如果什么事你都一个人抗,那么又将咱们这些年的情分放在哪里?”沈霖叹一口气,声音有点低沉,“你怎么会受伤的?”
“旧伤,”无从否认,我也不敢直说,只模糊道,“当时没在意,不动手也觉不出严重。”
“现在觉出来了?”他有些无奈的抓过我的手腕,扣住垂眸静默了一会儿,再看我时皱了眉,“你这伤原本不重,怎么会拖着?刚才这样大动气力又添损伤,再拖下去会动摇根基的。”
我点着头,低声:“我知道了。”
沈霖睨我一眼,轻蹙了眉,没再追问什么,只领着我回到王府,至药房绞了个浸了药的热帕子给我敷右手,不忘继续数落我:“以为揉捏几下就能好了么?说过多少次,骨骼一旦损害是永久的,气血经脉上的损伤更不可轻视,又不是没有条件治不了,你偏就不听。”
我不敢狡辩,唯唯称是,他见状叹口气,换了个问题:“在宫里过得好么?”
见他没有继续纠缠于我的伤,我也松一口气:“怎么会好?那天他发好大的脾气,第二天就帮着贵妃架空了我,然后又一直不露面,薛家处心积虑地要把我按下去,有什么事都想扯点罪过到我头上,太后杵在那,也没人敢靠过来——”
“孤立无援,四面楚歌,”我给自己的现状做了总结,很快又兀自笑了一下,“我的口气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怨妇?”
沈霖没有答我,少顷道:“即使这样,你依然很开心?”
“是,”我垂下眼睛淡笑,“至少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他身边,想见他的时候不必对着一堵红墙发呆,就算依然见不到,每天也会有人来跟我汇报他的行踪。”
“落影,”沈霖的声音温和如旧,满溢着叹息,“你要明白他的立场,他必须——”
“我当然明白,”打断他,我表达着自己的清醒和坚定,“容成家是他的心腹大患,这个皇后注定是颗棋子,早晚会被弃掉,既然如此,是别人,还不如是我,至少我可以在有价值的时候合他的意,在该消失的时候给他省些麻烦。”
顿一下我又道:“别叫落影了,我是锦言,不必管那个姓氏,叫我言言就好。”
“言言,”沈霖也是默然片刻才开口,“你明白的事他当然更清楚,只是和容成家的抗衡并非你想的那般简单,这里面的水太深,没人有把握胜出,你以这样一个身份陷进去,将来无论哪边得势可能都很难全身而退。”
对上他的眼睛,我知道沈霖说的话就是景熠想要说的,我没有附和也没有反驳。
跟着傅鸿雁回到坤仪宫时天已经偏了黄昏,才进屋就有人来报,说瑞祥宫的兰嫔一个时辰前小产了。
进宫不过十日,对于兰嫔,我只能说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,家里是个四品的大理寺少卿,属于还算得宠但兴不起风浪的那种。
“小产?”我皱眉看着眼前的水陌,十分意外,“她有身孕?”
水陌点点头,撇着嘴道:“都两个月了,不知道是迟钝还是故意瞒着不说。”
“瑞祥宫没有主位,早说出来一样保不住,”我一时并没放在心上,“还有别的人来找过我么?”
“没,”水陌摇头,后又跟了一句,“小姐,你要不要去那边看看?”
我迟疑了一下,问:“皇上知道了么?”
“知道,但没什么动静,太医这才报了咱们这边,”这些日水陌俨然做的功课比我多,“虽然只是个嫔位,但瑞祥宫是原来德妃的地方,昨天又刚出了慧妃的事,这个时候你是不是——”
“嗯,”我点头,“去一趟吧。”
匆匆换了衣裳妆饰,我到了瑞祥宫。
到了瑞祥宫,下人见了我都跪了下去,一问说是贵妃刚刚派了人过来瞧,没想到我这边能亲自上门,我摆摆手叫他们起来各自去忙,便迈步进了屋。
其实在我心里是不愿意跑这一趟的,一旦插了手,后头就要时时关注,不然有什么事还是会扯到我头上,不是什么重要的人,得不偿失就不划算了,贵妃不露面想来就是有这方面的考量,更何况是身边事还一团糟的我。
不过是如水陌所说,我的确需要这么一个出面展露态度的机会,也好给那些明眼聪明的看个风向,让那些愚笨糊涂的也早点露出本相,至于这兰嫔,万一是个可用的,以后还能派上点用场。
进屋的时候我暗自决定不再跟自己过不去,话都不必多说,进去转一圈摆个样子就走。
然而在我跟着引路的宫女走进兰嫔寝室的刹那,脚下还是突然一顿,面对着挣扎着要起身的兰嫔,我话都忘了说。
这屋里飘逸着的淡香,分明就是当年沈霖配出来,导致阑珊唐桀成仇的那药的味道……
我清晰地记得阑珊问起药性时沈霖回答过,避孕,且受孕三个月内的都保不住。
回到坤仪宫时心情有些复杂,一进门就又有人来报信,这回报的却是,景熠来了,正在漪澜殿里等我。
心里一沉,他这个时辰来,肯定知道我去了哪里,有事自会派人去找我,若无事,如此大张旗鼓地等在正殿里又是什么意思。
世事总是有很多意料之外,无论是瑞祥宫还是坤仪宫,迈进门时依旧是一顿。
漪澜殿内,景熠没有在主位落座,而是慵懒歪靠在一侧的椅子上,此时正陪着他说话谈笑的,是容成耀给我陪嫁进宫的两个美貌丫鬟。
拖着有些疲累懈怠的身子,我慢慢地走进去,先看到我的是佳莹佳玥两个,总归是带着心虚,话也没说一句就跪了下去。
景熠停了一下才转过来看我,迎上他的目光,我唇齿微碰,垂眼开口时依旧平静:“皇上。”
“嗯。”他淡笑着应,摆摆手示意两个丫头出去。
他的娴熟衬托了我的生疏,单独相对的时候,他不先开口,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开场白。
此时的他维持着那个舒适的坐姿,一副有的是时间耐心耗下去的表情,让我犹豫了一下,问他:“皇上这么晚过来可是有什么事?”
他一挑眉:“没事就不能来?”
“当然不是,”我勉强笑一下,胡乱找了个话题,“皇上可曾用过膳了?”
似乎没料到我会说这个,景熠唇边一弯:“没,这不是在等皇后一起。”
说着他扭头去看候在门口的蔡安:“传膳。”
早已过了晚膳的时辰,我不相信景熠还没有吃,原本是想着他说吃过了,我下一句就劝他早点休息,没想到他竟然顺着我的话传了膳。
蔡安连忙去张罗晚膳,我却有些懊恼,若在别日,我当然希望他多留一会儿,现在只会更添尴尬和焦躁。
用调羹搅着眼前的一碗汤,我努力掩饰着自己的些微无措。如沈霖说的,身上的伤的确是不能再拖,越来越强烈的气血逆上来,兀自压着耗去我太多的精神内力,面对一个敏锐犀利的他,我瞒不了多久。
“皇后没有话要说么?”景熠说话的时候头都没有抬。
我静默片刻,道:“外面的事都办完了,刚回来就听说瑞祥宫那边——”
“嗯,”景熠抬眼看我,“还有呢?”
我愣一愣,却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汇报,一时哑然。
少顷听到他的声音:“以后这种事,贵妃不去,你也不必跑。”
“是。”
不管他是在教我还是教训我,我都老老实实地点了头。
想了想里边的利害关系,还有兰嫔殿内那股幽香,我斟酌开口:“兰嫔家里虽然不算重臣,毕竟是有些头脸的,是不是要给些抚恤。”
他看我一眼:“如果你需要,明儿个会有旨意。”
我愣一下才明白他的意思:“谢皇上,臣妾不需要。”
忍下了皱眉的冲动,却没有忍下想说的话:“好歹相伴了几年,何必这样无情。”
景熠的脸上看不出喜怒:“皇后在教训朕么?”
我淡淡的笑:“我哪有什么资格教训你,只是想跟你说,我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,也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这个皇后如今是缓兵之计,以后会是吸引攻击的靶子和诱敌深入的棋子,就像我右手里的剑,平日里用得再多,都不过是迷惑对手和掩饰自己的手段,早晚——是要松开手弃掉的。”
“既然如此,”我紧跟着道,“这个位子由我来坐,至少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,你只需要看紧前面的敌人,其它的事,交给我。”
景熠盯着我,立起身子,转过去并不看我:“无论我要做什么,自然有我的方法和手段,不需要你这样无欲无求的牺牲,因为大凡无欲无求,将来都会问我索要更加巨大的回报。”
我注意到他自称的变化,轻轻一笑:“你需不需要,已经没得选择了,你总不能现在就废掉我,那可不是走一步废棋那么简单。”
“再说——”我淡下面色,“谁说我无欲无求了。”
放下手里一口都咽不下去的汤,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,看着他的眼睛:“你在人前怎样对我都没关系,大可按照你的计划去做,我不会退缩,更不会放弃,我只希望在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,你能卸下那些严密包裹自己的伪装,让你可以有一个地方,有一个时刻,能放过自己,也放过我。”
话虽然是这样说,我也知道让景熠卸下他已坚持了十几年,几乎已经成真的那些凌厉无情是何等艰难,不可能是一两句话可以动摇的。
“就算卸不下也没关系,”看着他依然毫无表情的样子,我轻叹一口气,将身子凑近他,“至少我们不要这样冷冰冰的虚与委蛇,至少你可以像对待其他妃嫔那样对我,能看到你爽朗谈笑我也很开心。”
我的退而求其次总算让他有了反应,他的眸子很快收紧了些,一只手突然揽上我的腰:“是么?”
“……是,”极少让人近身的我微微一颤,身子立刻就紧绷了些,勉强应了一句,“皇上要是吃好了,是不是——”
“嗯,”他挥手叫外头的人进来撤掉膳桌,揽着我就往内室去,“是该歇着了。”
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,也不敢跟他挣:“皇上——”
被他一直挟持到床榻前才站定,他低头道:“时辰太晚了,只好睡在皇后这儿了。”
他同样一副退而求其次的表情:“更衣吧。”
我顿时呆滞,有点玩火自焚的慌乱,好一会儿才讷讷地伸出手去。
才解开他的外衫,他带一点玩味的声音传来:“皇后方才还说希望朕像对待其他妃嫔那样,怎么这会儿又怕起来?”
我抬头看他,知道他是故意的,我此时要是退缩了,也许他再也不会重现这一刻,我咬咬唇,还没忘了进宫前被灌输多遍的那些规矩:“皇上还没有沐浴。”
他深看我:“皇后需要么?”
我低头不语,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,一旦泡在热水中,恐怕一刻都撑不下去。
我还没有想到应对的办法,他却已然不耐烦起来,伸出手脱了自己的衣衫,又来扯我的,夏日的衣裳本就少,没两下就被他极为熟练地褪了去。
被覆压着躺下的时候,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让我整个人都僵起来,原本压制着的气息一下子就岔了,绞痛传来,忍不住闷咳几声,为免露馅,我不敢开口说话,连忙挣扎着想要起身。
景熠眉头微皱,手上力道加重不让我动弹,随即出手如电,点了我胸前四处大穴,语气有些低沉:“知道为何宫里不能容会武的妃嫔了么?”
大穴被封,内力彻底被封掉,胸口的痛反而暂时有了好转,身上软下来的同时,景熠的吻覆下来,喑哑的声音若有若无:“你没有机会再后悔了。”
瘫软之下并非不能动弹,我只不过是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女子,面对帝王临幸,是何等荣耀欢喜。将手轻轻地抚上他光洁坚实的背,紧张之余开始小心而又热烈的回应,迎合并加深那个吻,无声地告诉他,我很高兴,我不会后悔。
听着枕边景熠平缓悠长的气息,我轻轻地转过头去看他,不禁开始猜测他睡在其他女子身边的时候是否也是这般平静,那些女子在这样看着他的时候,又会是怎样的心情。
想着想着,唇边的那抹微笑渐渐消失,不光因着那些可想而知的画面,身体里翻搅着的闷痛也让我意识到,这一日夜的状况已经彻底恶化了十日前的内伤,现在还不到子时,我恐怕撑不到天亮景熠离开。
真的很累了,却丝毫睡不下,又不敢轻易移动,终于在连吸气都痛得有些痉挛的时候,我慢慢地撑着身子坐起来,穴道还没有到自解的时辰,阻塞的气血咳不出来又压不下去,我弓着身子硬扛了一会儿,还是决定去拿沈霖给我带回来的伤药。
不想才伸腿套上鞋,还未起身,手腕就被一把抓住,景熠的声音低沉慵懒:“要去做什么?”
我心里一惊,转头:“吵醒皇上了?”
他动了动身子,手却不肯松开,模糊道: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我轻拉了一下,扯不出手,于是顺势把身子滑下床,半跪在他枕边:“皇上歇着,臣妾去去就回。”
他却一句话就浇灭了我的奢望:“后宫里人人都盼着伴君天明,唯皇后有这个名正言顺的资格,为何却要离开?”
我咬唇不语,许久后,终是服了软,低声开口:“你能不能,帮我把穴道解开。”
屋里只有一盏小小的守夜烛火,并不明亮,我看到他睁开眼睛看我,也许是刻意,也许是偶然,此时的他目光温和:“你已经压不住了,现在解开,内力反噬出来,岂不是伤得更重。”
我愣住,少顷才道:“你——早知道了?”
景熠也坐起来,看着我道:“沈霖傍晚进宫来,无故说了些没好气的话,我就猜一定是你有什么事,这一晚上跟你近身在一起,我要是还看不出来,也就做不得这个皇帝了。”
我眨眨眼,不明白沈霖怎么会找上景熠:“沈霖他怎么——”
“我与他练的是同宗内功,能造成什么伤害,他再清楚不过,”景熠摇摇头,向我伸出手,“过来。”
我愣愣地凑过去,想起下午沈霖给我诊伤时候的莫名沉默,想起晚上自己费尽心思要瞒的都是掩耳盗铃,心里忽地就生了怨怼:“你知道还故意这样对我,一定要我自己来求饶才满意是不是?”
“原来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阴险邪恶的人,”他斜着眼睛看我,眉宇不见舒展,“你气息都乱成那个样子了,不封掉穴道沉淀一下,就打算强行疗伤么?”
少顷景熠轻叹一声:“你练的内功庞杂,受了这种精纯的伤,怎么能拖着不理?为何你要我卸下防备,自己却不肯坦诚相待,我本无意伤你,你却拿身子来跟我较劲。”
“沈霖给你的药是不能在发作的时候用的,不然只会治标误本,你不会不知道,可我要是今晚不来看着你,你才不会管那么多,是不是?”
知道他所言全都不假,我别开眼睛不出声。
他将手抵在我背心,温热内力帮我压制着蹿上心头的气血,让我好过了些之后才悠然道:“你好歹是皇后,在宫里出点什么状况,要朕怎么跟家国天下交代。”
听着他复又冠冕堂皇的话,我配合着应:“谢皇上关心。”
他却轻哼一声:“是不是又想说,皇上给的教训,你记住了。”
我怔一下,转过头去看他,没想到他把半年前这句话记得这么清楚。
此时的我半靠在他怀里,以这样一个暧昧又温情的姿势听他说起旧事,总是有些怪异,他并不看我,只低头问:“手上的伤都好了么?”
“沈霖这样问的时候,我说都好了,连疤都没落下一个,”我伸出右手动了动,“可是如果你问,我会告诉你,它只是看起来好了,实际上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,还是痛到几乎握不住剑。”
“这种说法上的差别,”他挑眉看我,“是为了让我内疚?”
“你会么?”淡然反问一句,我兀自笑了笑,“当然不是,只是想告诉你,我为什么会跟慧妃过不去。”
他愣一下,似笑非笑:“哦?”
我看着他道:“我想我不能天真的以为你没看出来,虽然巫蛊之事与我无关,但始作俑者是我。”
“嗯,”他停一下道,“当时的事与她有关?”
“我一直以为当时闯进政元殿的就是她,后来见到才知道不是,既然动手之人句句表明受人指使,一些刻意嫁祸的迹象也就十分明显了,毕竟能有几个人知道当日平妃进出和遇到我的细节呢,”我摊摊手,“想来总是与她脱不了干系,刚好又是贵妃的人,你帮着她们架空我,我自然要找个出气的炮灰。”
他的笑漾开来:“做得很好,简单有效。”
被他称赞,我有点受宠若惊,讷讷着:“那个平妃,要我做点什么把她弄回来么?”
他一时没说话,反而是抵住我后背的手突然发力,剧痛让我弯了腰,一大口血呕出来,我胡乱的抓了件衣裳来接,又咳了两声之后感觉血脉通畅起来,他扶着我,随即帮我解开穴道。
这时候他接上方才的话题:“那是个愚笨的,弄回来也派不上用场,早晚连命都保不住。”
“哦。”从他的话里我听到了一些言外之意,却一时没能明白,我知道他能肯跟我说一些话已经很难得,也没有再多问。
他却意犹未尽:“怎么不再说什么好歹也是相伴几年的话了?”
疲累袭来,我有点打不起精神,轻笑着:“那话是皇后说的,皇上想听,臣妾还是可以勉为其难。”
他看着我也是笑,直让人贪恋着挪不开眼睛,过一会儿他才淡淡地问:“你就那么确认当时不是我指使的?”
“嗯——”
我窝在他怀里贪图着刹那柔情,伸出右手晃了下,喃喃道,“你不会做没价值的事,如果是你指使,不会是这只手。”
经久沉默,他将手在我后背上拍了拍:“去睡一会儿吧,一月内都少要动用内力,沈霖会送药来的。”
我无声点头,酣然入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