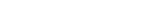初秋的殷都,清晨已经开始很凉,用嘴能呵出些许白气。
冯愉和乔培安侯在东偏殿门口很久了,久到冯愉用绸带松散绑起的乌发和长睫上都沾了些点点晨露。冯愉直接伸手把发带散了,长发披散在肩上,在雾蒙蒙的早晨,为他平添几分朦胧的柔美。
“易欢这是等不及了?”乔培安调侃他。
“没有的事。”冯愉欠身笑笑“只是怕见公主时形容欠佳。”
乔培安目光带了几分深意:“我只当易欢兄一直是云淡风轻,不争不抢呢。”
冯愉突然理解公主喜静了,与人交流有时真是需提起十二分精神,他打着哈哈:“乔兄别折煞我了,冯某是俗人,所图也只有公主的垂青而已。”
“巧了,乔某也是,那我们俩算是对手了吗?”乔培安眯起眼,却仍保持着风度,像一只感受到危险的豹子,身上的毛都竖起来,尖利的爪子试探着伸出,嗅着任何潜在敌人对它的威胁。
不知冯愉是没注意到乔培安的变化,还是真的不怕,他还是那副淡淡的模样,漫不经心地说:“那乔兄已经赢了,冯某差得远呐。”
一记重拳打到棉花上,这点乔培安倒是没想到,他脑子里飞速运转着,还想对冯愉发难。
“呀,你们来得这么早。”公主寝宫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,朝阳公主被身边的宫女簇拥着走出来。
“不知公主几时启程,不危就早早来这儿候着,即使冷着也不能让公主等。”乔培安敛起了刚刚的锋芒,对着朝阳公主又是一幅风度翩翩的模样,他把话抛给冯愉:“易欢说呢?”
“……”冯愉一时无言,好话都让他乔培安说完了,还不忘点到自己。他看向公主:“……正如乔兄所说。”便没了下文。
公主踱步到两人身边,转向冯愉,纤纤细手撩起他半湿的长发:“易欢头发都湿了,若是着凉,我可就是罪人了。”
“怎会。”冯愉望着公主笑了,剩下的话并不说,只含在那一双眸子里,桃花眼含情脉脉地看着公主。
可惜,朝阳公主并不接招。
“走吧。”她踏上特制的檀木马车,留给其他人一个背影。
冯愉和乔培安分别跨上宫人牵来的马,一行人徐徐向宫外走去。
朝阳公主今天着一身素月牙白长衣,腰间系一个旧旧的香包,那是皇后在她幼时亲手绣给她祈福的。
“公主,一会儿可能会下雨,把罩袍披上吧。”小莲给公主穿上鸦色罩袍,只剩公主一张略显苍白的容颜隐隐约约半掩在兜帽下。小莲把衣服上的褶皱细细抚平,她心疼这样的公主,想着找些话与她说:“太子殿下的队伍已经和我们回合了,走快些兴许下午就能到皇陵。”
公主点点头,不语,她掀开帘子一角,已经淅淅沥沥下起了毛毛细雨。
她吩咐小莲:“让乔公子冯公子上我的车来避雨吧。”
外面马蹄声渐近,乔培安撩起帘子,跨了进来,却没见着冯愉。公主微微侧头问:“易欢怎么了?”
“回公主,冯某担心身上雨水寒气凉了车内,命小童拿了罩袍换上再进来。”冯愉的声音从车外传来。
乔培安开着玩笑:“易欢兄可真磨蹭。”他还没说完,却惊讶地发现,公主的嘴角扬起了一丝转瞬即逝的笑意,不同于平常应付他们的像模子里刻出来的笑,而是像小女儿家从心底溜到嘴角眉梢的甜意。公主莫不是对这冯愉另眼相看了?乔培安心里一惊,期望自己是看错了。
冯愉抖落身上的雨滴,坐上车,颔首对公主算是致意,公主也点点头,没有交谈。
车内气氛过于安静,乔培安试图打破沉默:“公主和易欢兄知道这皇陵选址时的波折吗?”
“不知道。”冯愉笑笑。
“那乔某就献丑给说说自己知道的吧。”乔培安清了清嗓子,准备开讲。
公主毫不客气地打断他:“我不想听。”
……好不尴尬。
乔培安面上还是礼貌地笑着,看不出被公主噎到的模样:“既然公主不喜欢,那我换一个,公主喜欢志怪小说吗?”
“不喜欢。”
“那公主想听什么?”
“我什么都不想听。”公主一直埋着的头突然抬起,幽幽地盯着乔培安,看得他后背一凉。“乔培安,你到底懂不懂,我需要的只是安静而已。”
这回乔培安真没法给自己找台阶下了,当着冯愉的面被公主这样给了难堪,就算是普通的男子也会自尊心受挫,更别说是养尊处优的乔家大公子了。他仍然好生端坐在那儿,只是脸已经涨红,胸口也微微起伏着,袖子下的拳头已经攥成一团。
冯愉把头扭向窗外,事不关己的模样,公主直接是合上了眼小憩。
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理智,乔培安弯着腰退向车门:”那乔某就不再扫公主的兴了。”说罢,叫停了车,冒雨下去了。
两人间一时无言,但也不觉得尴尬,显然都各自有心事。
公主突然开口,许久未开口,嗓子有些沙哑:“我讨厌他总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”
冯愉自然知道公主指的谁,倒了杯热茶递给公主:“不危兄只是想讨好公主。”
接过茶,公主挑起眉看着冯愉:“我知道你看得出来他是什么人,但不想得罪人罢了。”
“公主何出此言?”冯愉耐心地往前坐了坐,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。
“乔培安自以为自己一定是最后的赢家,可惜他低估我了。”公主把手环抱在胸前,冷笑了一声:“打仗时最愚蠢的事情就是低估对手,总以为除了自己都是傻子是吧。”
冯愉靠得更近了些:“冯某倒是觉得公主高估了我。”
公主并不多,兴致勃勃地与他交锋:“你知道吗,我觉得也许我们是同一类人。”
正想继续追问,马车却突然急急刹住车,公主一下栽到了冯愉怀中。
“怎么回事?”冯愉皱眉问向车外。
未曾想,回答他的是几支冷冷的箭,飕飕地带着凉气,狠狠擦过冯愉的肩头,钉进对面的木头里。
把公主紧紧护在怀中后,冯愉余光看到自己的衣服已经破了,还擦破了点皮,正在渗血,半个箭头已经没入了木板里,看来射箭的人是用了十足的气力,决意要取车内人的性命。
“快下车!”公主当机立断,抬起头对冯愉喊着。
用宽大的衣袖罩住公主,冯愉带着公主迅速逃下了车。一下车,眼前的场景十分骇人:车夫被一箭穿喉,射死在马上,脖子上一大个窟窿还在汨汨冒着血。宫女和其他乔培安等随从的被拦在后面,只剩下太子和公主的马车孤零零在路上停着。
为了赶时间,他们这次走的山中小道,树木丛生,根本看不到箭从何方来,敌人又躲在哪儿。除了一侧的山壁,马车另一边就是无底深渊。
太子被仅剩的几个侍卫护着,吓得面无人色,踉踉跄跄地从车上滚下来,奔向公主:“朝阳!朝阳你没事儿吧!咱们快逃吧!”
朝阳公主好歹是上过战场的人,已经镇静下来,从冯愉怀里挣脱,一把拉住太子躲到一丛灌木后。
冯愉地怀中突然空了,有些可惜的摇摇头,也跟着躲了过去。
箭并没有再射来,公主抓住空当问太子:”你还剩几个侍卫?”
太子哆哆嗦嗦伸出两个手指,眼中涌出泪水:“跟了我十多年的侍卫长刚刚为了保护我没了,我们……我们会死在这儿吗朝阳?”
然而公主并没有时间理会太子,她计算着身后的侍卫能多久来接应他们,如果敌人过来她又能撑多久。
“朝阳……”太子拽着妹妹的衣袖,眼泪还是不住地流着。
朝阳公主耐心地拍拍太子的肩膀:”哥哥,听我说,一会儿有人上来的话,你就上他的马,带上剩下的侍卫一块儿走。”
太子的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:“不行,朝阳,我绝不会把你留在这。”
“你听话,我有武功傍身,不要紧。”
听到听话二字,太子的眸色暗淡了几分,却依然坚持:“那你也得跟我一起走。”
正在此时,弯道上传来阵阵马蹄和乔培安焦急的呼喊:“公主!太子!你们在哪儿?”
见救兵来了,公主毫不犹豫地把太子推出去,太子毫无防备,在地上摔了个大马趴。“带太子走!下山找救兵!”公主说完,拉着冯愉往山壁最低处爬。
乔培安脸色大变,拉起太子上了马,对着公主大吼:”朝阳!随我走啊!你要去哪儿?”
见人都显了身,躲在暗处的敌人又开始了一波箭雨的攻击,两个侍卫忙挡在前面力不从心地用剑挥开,为太子争取些许宝贵的时间。
公主没有理会他们,和冯愉一前一后爬上了顶。乔培安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,狠心一咬牙,一抽马鞭:“驾!“冲下了山。
冯愉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力气,跟着公主就爬上了断崖,一翻过去,竟是一片茂密的森林,他单膝跪在粗粝的石地上喘气,却被公主一把拉起来。
“可不敢在这儿停下。”公主硬是拉着他,连拉带扯,跌跌撞撞进了森林。
皇陵位置在都城郊外,并不很远,但是由于是皇家的地方,平日根本无人靠近。朝阳记得父皇说,这地方幽静,风景又好,母后定会喜欢的。没想到今日倒是被这个地方救了一命。
他们俩都穿着宽大的袍子,行动十分不便,干脆都脱了下来,冯愉把破的袖子撕成一条条的布条,拴在沿途的树上。
“你还挺细心。“公主一边调侃他,一边把裙子塞进腰间,只剩里头的白色长衬裤。”等等……“她突然敛了神色:”好像要下雨了,我们快些走。“
“下雨怎么了?“冯愉不解。
公主的的眸子暗淡了下来: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没有再继续追问,冯愉走到公主前面,扒开杂乱的枝条,清理的前面的路,时不时在难走的地方拉公主一把。
好不容易看到一条小溪,旁边有个低矮的山洞,两人如释重负,收拾了一番,天已经黑了。冯愉让公主先休息,出去找干草和枯枝。
晚上的森林里太冷了,冯愉没了外袍,有点开始发抖。这里的森林过于茂密,把天空严严实实挡住,连一点星光和月光都没法投下来,冯愉担心公主,匆匆在黑暗中随便捡拾了枯枝,就摸黑回去了。
然而公主并没有呆在洞口,往里看去,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,冯愉慌了神:”公主?你在里面吗?”
里面过了半天,传来像小猫一样,孱弱的呻吟声,断断续续的,掺杂着极大的痛苦。
冯愉吓着了,立马弯腰爬进去,借着外面小溪反过来的点点微光,看到公主躺在一块石板上,小小的身体蜷成一团,难受的喘息急急地透出来。
小心翼翼抱起公主,冯愉把她圈在怀里带到洞口,才看清,公主的脸已经煞白,豆大的汗滴从鬓角滑入脖颈,牙齿把下唇咬出了点点鲜血,双手抱着膝盖,指缝把月白的裙子夹得紧紧的,整个人狼狈得一点也看不出是个在深宫里养尊处优的公主。
“哪儿疼?“冯愉用袖子给她轻轻拭去汗水,拍拍她的脸,试图让血迹斑斑的下唇被松开。
阵痛过去后,公主缓了过来,把脑袋偏开,不愿看冯愉。
冯愉知道,一向高傲的公主,以这样狼狈的姿态出现在自己面首的面前,又刚刚经历这样大的病痛,心里的滋味,只有她自己能说得清有多难受。况且,公主这样的痛,看她在要下雨时说的话,就能知道一定不是第一次,却从来没听宫里任何人提过,或许是知情的人想要极力保守的秘密。
不愿再勉强公主,冯愉把她放到干草铺好的地方,转身去溪边用剩下的布条润湿给公主擦擦汗。
刚一转身,公主就喊住了他:“别走。“声音已经沙哑得不行,带着一点哭腔,冯愉的心突然被击中,几乎是立刻回到她的身边。
“我不走,只是去接水给你擦擦汗。“冯愉伸出手温柔地拍着公主的背,像哄一个婴儿。
朝阳被安抚着,紧缩的身体渐渐放松开,委屈地撇撇嘴:“腿疼。“
“失礼了。“冯愉手按上公主的腿:“膝盖还是脚踝?”
“左腿,膝盖以下,到了下雨天都疼。”
为了更好地帮公主按摩,冯愉把公主抱紧怀中靠着他坐着,朝阳的头倚靠在他的胸膛,他一寸寸地耐心帮公主按着腿。看着极暧昧的一幕,两人之间却没有旖旎的心思。
外面浠沥沥下起了小雨,冯愉脱下中衣,披在公主身上,只剩一件单衣薄薄的穿着。
“这伤是我打匈奴时留下的。”公主突然开口,她的目光越过冯愉的肩看向洞外,看到了很远很远的以前。
“我们人太少,我从马上摔了下来,受惊的马从我腿上踩过。听大夫说骨头都碎了,正好遇上一位神医,给我治好了。”惊心动魄攸关生死的事,从公主的叙述中却显得平淡无奇,就像被割破了手指一样寻常。
“阴雨天会疼是后遗症吗?”冯愉问到。
“嗯。走路也很慢,时间也不可太长,会很疼。”公主顿了顿:“你答应我不要告诉别人。”
冯愉失笑,这时候这小姑娘的警惕性都这么高:“我发誓,不说出去。”
在冯愉怀中坐直,朝阳的眼睛亮亮的,在黑暗中比雨幕里的星光更明几分。
“其实我不是喜静,是怕声音,大一点点的声音我都怕。”朝阳公主说着,身上又开始发抖:”战场上,是很吵的,马蹄声,战鼓声,吼叫声,兵刃声……”
她是帝国的公主啊,被最尊贵的皇上皇后捧在手心里长大的明珠,长在宫中,听到过最嘈杂的,不过是宴会上的觥筹交错和丝竹之声。金戈铁马本是与她半点不相关的事情,冯愉想象不到,在他怀里的这个小小的女孩子,穿上盔甲,指挥千军万马上阵杀敌时,心里瞒下了多少恐惧和委屈。从天上人间到了血海地狱,她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吗?
“回来之后,我再也听不得任何吵闹的声音,不然会控制不住地发抖,害怕,流泪。“公主抬起头看着冯愉:”所以我不是那种刻薄之人,故意拘着你们……“
“我知道。“冯愉回以她温柔的眼神,三个字足以让公主安下心来。
“别怕。“他搂着公主,吻吻她的额头:”以后冯愉在宫中一日,决不让吵闹惊扰公主。“
公主没有回应,因为她惊讶地发现,自己的疼痛正在减缓,她惊喜地问到:“你这是什么按摩手法?我竟然不怎么疼了。“
冯愉笑得一脸高深:“冯家祖传,秘密。“想了想又补到:”以后阴雨天,还望公主提前允我到宫中为公主解忧。“
公主有些不满:“我都告诉你我的秘密了,你总得有点交换的东西。“
“好好好。“冯愉哄着她,一双桃花眼笑得公主有些陷进去了,”那我给公主说说我为什么会学按摩这种服侍人的吧。“
冯愉说过,自己是小地方来的——营城冯家的人。营城确实不大,可大殷若少了营城,整个南北都会断了来往。大殷的版图,南北都宽,中间极窄,像一条细细的线连接起了两个重物,这中间的城,就是营城,链接着南北的商贸通信,还与东西其他国家都接壤,在地势上可谓是重中之重。
冯太守是冯愉的父亲,他们冯家历来把守营城重镇,世代相传。不得不说冯家不仅有手段,把这样一个商贾来往,军队驻扎的小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,从来没出过乱子,还对皇家忠心耿耿,每年上交的税和粮是最多最好的,皇上每次提及冯太守,都是赞不绝口。
可是但凡是人,总是有缺点的,冯家枝繁叶茂家大业大,冯愉父亲在此中脱颖而出接替了太守的位置,才能和衷心都是一等。不过百姓提起冯太守,夸赞完后,嘴角都要带一丝暧昧的笑,补一句:“只可惜冯太守太风流啊!“
冯愉是他父亲第七房小妾的儿子,冯太守不仅有正妻,还有十多个妾室,今天去这个杨柳腰屋里,明天陪那个芙蓉面,就连他自己有时候都分不清他有多少个妾,在烟花之地也是经常有他处处留恋的身影。冯愉的母亲,就是青楼里的头牌。被冯太守包了下来,怀了孕,迎进了家门。
冯愉记得母亲极美,她身上每一处都会撩人,举手投足都是说不完的风情。只可惜再美的女人,被丢进十几个女人的后院,也会枯萎的。年幼的冯愉看着母亲一天天凋谢,不知道在哪天突然明白了,前途得靠他自己挣。
冯家有钱,从不曾苛待一个孩子,大家吃穿用度,上的学堂都是一样的,如何在父亲的十多个孩子中露头,让父亲宠爱自己,是那时候的冯愉每天琢磨的最多的事情。还好,他的母亲在青楼里,最会的就是读人眼色,服侍别人。求着母亲,冯愉学会了很多东西,知道斟茶是如何压水花和茶末,懂得了在要讨好的人生气和开心时分别奏什么曲,当然也有今天救了公主的这套按摩的手法。
他从不觉得这些东西低贱,所以即使有人喊他是哈巴狗他也毫不在意,冯愉只知道他靠这些为母亲重新赢回了父亲的宠爱,还有对自己更多关怀。
不过,冯愉总是会想,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更大的事,能把自己优势发挥到极致的事。
所以当听到公主需要面首时,他毅然找到父亲,跪下说:“儿子自愿入宫服侍朝阳公主,为冯家分忧。”
然后他在那天的深夜里,被带到公主宫里,听到公主那宛如黄莺的声音说:“那个有泪痣的,也留下。”
从那时起,他们的故事就开始了。